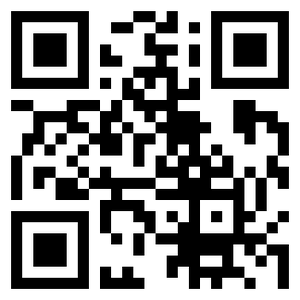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新作《浪浪山小妖怪》正在全国院线热映太原炒股配资,赢得了豆瓣评分8.6的高口碑。这部适合全年龄段观影的作品,精准捕捉并呼应了当下的观众情绪。

《浪浪山》是动画短篇集《中国奇谭》(2023)中高口碑短片《小妖怪的夏天》的衍生电影。影片延续了小猪妖的故事、“Nobody”的精神内核,以及独特的水墨美学风格。这个故事生动地呈现了小妖怪们“出发吧,不要问路在哪”的无畏果决,却止步于“敢问路在何方”的追问中。

2023年,《小妖怪的夏天》让那个天真的小猪妖深入人心。短暂归家的小猪妖仰望洞口飞过的小鸟,喃喃自语道想离开浪浪山,这一幕引发无数观众的共鸣。“离开浪浪山”迅速成为网络热词,象征着人们对逃离舒适圈并寻求改变的渴望。

《浪浪山》并非短片的简单延续,更像是平行宇宙中的“小猪妖重生记”。它并非对《西游记》的戏仿或新编,而是潜入宏大叙事的裂隙,照亮了那些未被书写的鲜活小妖怪。当正版的西游故事退为背景板,以小猪妖、蛤蟆精为代表的原著中微不足道的反派小角色,其个体形象便被凸显出来。

长片中,小猪妖只是浪浪山的临时员工,为博取大王的青睐,甘愿自我异化为“工具人”,利用自身优势甘当“刷锅球”,却因表现太过“出色”而“喜提死刑”。此时的小猪妖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,只能为了活命而孤注一掷。他与蛤蟆精、黄鼠狼精、猩猩怪组成了“冒牌军团”,冒用唐僧师徒四人的身份,想要抢先一步到达西天,夺取真经。

《浪浪山》和《长安的荔枝》似乎也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,都向观众抛出了一个沉甸甸的问题:假若终点凶多吉少,还要启程吗?它们给出的答案是“我来过,奋斗过,便无悔”。

在激烈打斗场面的闪回中,四个小妖再度忆起曾经的压抑与痛苦,同时奋不顾身地冲向眼前劲敌——哪怕终将籍籍无名,也要拼尽全力反抗。

离开浪浪山只是这个故事的起点,小妖怪一行四人在取经路上不断面对艰难险阻,影片渐渐揭示出:围困着他们的其实层层叠叠的“浪浪山”。小妖怪们经历了“看山是山,看山不是山,看山还是山”的三重境遇。

所谓“看山是山”是无知无畏的启程,小猪妖因为信息差误以为无论何人取得真经都能得道、长生不老;蛤蟆精虽求安稳却惨遭“连累”,在绝境中求生;流浪者黄鼠狼精随遇而安;猩猩怪则是被告知这是“唯一的出路”后被迫启程。这样意义模糊的起步,恰似当下存在的某种从众心理。

影片精彩的部分在于小妖怪们“看山不是山”的历程:一路上,他们遭致孩童嘲笑却也认清现实,得到老僧的信任,借助齐天大圣的名号换来双狗洞的欢迎,因合力斗败老鼠精而得到村民拥戴……种种经历让他们渐生幻觉,以为此路可行。

直到他们抵达小雷音寺时,一条“坦途”赫然摆在面前。穿上四大天王的甲胄,分得一口“唐僧肉”,对渴望摆脱挣扎的小妖怪而言似乎是符合本能的选择。但捷径背后的代价是,成为助纣为虐的一员,彻底被褫夺内心良善的一面。

在“看山还是山”的突破层面上,小妖怪们终于认清了自身的渺小,倾尽全力、耗尽修行,才能勉强击败黄眉怪。他们意识到自己被裹挟在更庞大、更隐蔽的“山峦”之中,黄眉怪实为弥勒佛为唐僧师徒设计的劫难,小妖怪的胜利对取经大局毫无影响。他们所能选择的是一条前无古人、属于自己的取经路。
影片行至此处,小妖怪们竭力找寻的取经之路,在他们斗败黄眉怪、救出孩子们后戛然而止。电影选择了一个过于理想主义且答案简化的结局,放弃了对“自己的取经路何在”的深层叩问,转向了惩恶扬善、无限放大小人物身上能量的圆融结局。
从画风上来看,《浪浪山》舒适入眼,却也缺乏一定的美学创新意义。影片追求的“大处写意、小处写实”的理念,被其中堆砌的网络语言和过分写实的情节所折损,“五行五色”等多处匠心设计也未能与叙事表达融为一炉。
值得深思的是太原炒股配资,从票房和口碑上来看,这部影片的确为不少观众注入了精神力量。但在影片与观众产生共鸣之时,我们更要对这种情绪高涨的类型叙事保持清醒。还有无数“Nobody”要前仆后继地踏上自己的取经路,而他们的故事应该没有标准答案,毕竟,路终究在自己脚下。
镕盛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